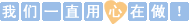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转变职教观念与“何不食肉糜”
2014-05-14 12:50 来源:新华教育 作者:采编 阅读:129次 我要评论
[导读]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发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近日,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教授在“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

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发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近日,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教授在“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就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学习欧洲的经验、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借应用型大学转型推动高考改革、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主体、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为什么学习欧洲
为什么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呢?胡建波院长最初的想法是,欧洲的教育主要由政府投资,政府有力量推动“双元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不由联邦政府决定,联邦和各州分权,各州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由政府主导直接提出应用技术大学的体系。
就这个观点,他请教美国杜肯大学教育学院伯龙教授时,伯龙教授说:“我不认为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我认为欧洲与美国在应用技术大学问题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欧洲社会对技能型工作给予尊重、从业者也会有很好的待遇和很好的社会地位。而在美国,从事技能型的工作不太被人尊重。虽然美国政府也试图把技术教育向前促进,但报考的学生往往被社会认为是学习能力差,素质不太高的人。事实上,报纸也经常披露州政府给这些学生的贷款,学生就业后几年仍不偿还,问题出现的比例还非常高,有些贷款机构为此还诉诸法律。”
总体讲,伯龙教授认为,美国和欧洲在技能人才培养的差别主要原因来自于文化差异。
很多专家都从国家教育比较的角度上讲老百姓应该如何转变观念,政府应该重视职业教育等等,但很明显,在对待技能型人才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文化特点是跟美国差不多的,和欧洲不一致。德国双元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真学他们能不能真的做到?
胡建波院长认为,谈到应用技术大学转型,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问题。美国与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劣很难讲,他个人以为美国的创新文化和德国的技术领先文化也是两国经济商业模式不同的原因,世界500强企业中,德国的精密制造技术让一批制造企业长期居于前列,排名基本不变,而美国创新文化特点,带来了创新企业层出不穷,排行榜上的企业此起彼伏,变化极大。
会前,胡建波院长还向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校长通电话求教,20多年来台湾的科技大学到底成绩如何?曾校长谈到,根据《远见》杂志对台湾高校就业调查的历年数据来看,就业最好的前10所学校中有5、6所是清华交大这样的传统公办名校,还有4、5所就是台湾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这类以就业为导向的科技大学,而这些学校之前的排位是非常靠后的。
胡建波院长又追问,请曾校长谈谈科技类大学还存在哪些问题?曾校长说,总体还不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升学主义”的问题。台湾学生是拿了专科想本科,拿了本科升硕士,拿了硕士想博士。学生不停要升学,科技大学的定位跟社会需求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胡建波院长回顾这两次谈话,是想引出他对后面几个问题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
民众对待技能人才的文化氛围和态度,以及对待学历文凭的态度观念是思考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
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大不相同。文凭不断向上发展是大趋势,一是原有的一些基础工作不断被工具、技术、机器所取代,现有的工作越来越需要劳动者具有批判性思维、沟通交流、组织规划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学历与提升社会地位相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已经超越了原有基于经济学思维的劳动分工理论。
胡建波院长经常碰到一些同志说当年中专的水平多高,大专水平多高,现在研究生都不行了!她想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文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他记着以前看《克林顿传》,克林顿当州长的时候将14所中专学校升为社区大学。文凭向上提升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德国也不例外。
胡建波院长给大家展示了一组数据,芬兰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里专科层次里只占生源比例的7%,台湾只有占到5%,而我们现在占到40%多。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就是不想上高职,就想拿本科文凭!回想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每月挣58.5元,而今天工资5000都未必有当年58.5元管用。
和货币的流动性问题一样,学历的向上提升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趋势 ,是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果,也是民众心理需要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既提升高等教育的层次,但没有像台湾那样特别放松,都在采取措施调控,逐步往上提。过度提升教育的文凭层次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一样当然是不妥的,现在要判别的是什么是合适的节奏,他个人以为目前中国显然没有所谓的过度问题。
我们现在上中职的生源,或者是因为高中考不上,或者是因为家庭收入低的,在当时希望赶快找一份工作,于是选择了中职。但上中职后,再想向上发展,只有三校生考试这一次机会上高职,录取比例还非常低。技校、职业高中和中专的学生,有几百万人分流在那,当前却只有十几、二十几万人能上高职、专科。这里面显然是条断头路,断了上了中职孩子们继续升学的路。
“升学主义”是亚洲的普遍现象,只可适应与顺势而为,打通职教,提升职教层次其实是发展职教的识时务之举,断头、强压的后果已经显现,职教成了社会中低层次、低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具体表现就是中职、高职这几年生源掉的很厉害,当前生源好的高职院校也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自知无法抵挡“升学主义”这个所谓的坏观念所带来的生源下滑的趋势。
此次教育部倡导应用技能大学转型,一是解决现有地方性本科高校毕业生没有围绕产业需求培养人才,带来的就业难问题。其次,就是试图解决“断头路”的问题。
山东省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学生上完三年中职,还想上本科,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极少数学生通过三校生高考可以进入高职学院。
大家知道,全国目前每年年高考录取大概700万人,专科的录取比例大约是45%,也就是说有300多万人上了高职,但其中仅有5%的人才有资格专升本,而且只有一次统一考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选择高职就很难继续升学,这与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很矛盾,所以高职报到率比较低,陕西省每年7万多人被学校录取但不报道,复读一年再考二本三本。
实际上北美的社区大学两年后相当大的比例转入大学继续读本科,如果高职有20%的比例转读四年本科,高职就不会为生存特别担忧。很多专家讲这个问题都是从社会对人才需求层面说问题,但是没有多关注学校层面怎么活的问题,只是希望职业学校转变观念,办好职业教育,不要盲目升格,可是它都没学生了,它转个鬼观念,这种话像极了晋惠帝所说的“何不食肉糜”。
第二个问题,借应用型大学转型推动高考改革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二十年高考改革并不到位,高考改革不仅要改考核内容,更要改招生录取方式。
高考改革为什么改不动,核心是万众瞩目,让所谓高水平大学985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火中取栗。可行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全国高校大概有700所是民办高校,如果能参照日本的方式,民办学校独立招生,自主招生,一下子高考的人数就锐减了,从法理上来讲,民办高校有办学自主权,又不是人人想上的学校,火小了,改革推进的风险、阻力就少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就更大。
如果这次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职业教育体系入学通道大打通,无疑对当前的统一高考彻底改革也有重要的解围意义。
第三个问题,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主体不一定是制造装备业
芬兰整个应用技术大学中比重最高的是社会科学占30%多,技术方面是10%几,整个欧洲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占了经济总量70%多,制造业20%,农业占10%不到。
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才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的变化也会带动教育结构的变化。我和查建中教授就这个问题还通过电话,他认为这次大学转型叫做应用技术大学值得商榷的,改叫应用科技大学比较合乎原词义,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技术加应用就多余了。
因此,这次应用型高校转型应该强调涵盖社会科学,包括创意产业、以及和IT技术等相关领域,而不应仅仅是工程师类的人才。
从欧洲、美国来看,我国的工科比例偏高,工科的主要问题是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真正落实到位,以及办学质量是否和国际接轨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第三产业必然是应用型科技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服务对象。
第四个问题,建议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
姜大源教授主张成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胡建波院长个人认为应该成立委员会,区别在于由谁主导。大体来讲,证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学历证书,这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学位证书,但这毕竟与行业的需求有所不同,学历的获取并不能完全代表从业的标准。
另一类是职业证书,现在部分职业证书已经很具含金量,比如ACCA、会计证书等等都非常严肃,有含金量。高含金量职业证书的影响力扩大客观上也是对学历流动性过剩的一种对冲。如果完全靠政府推动,比如前些年劳动部推出的证书,现实中几百块钱就能拿一个,真是有点不值钱!
因此,胡院长认为证书问题完全靠政府行政手段很难保证,有效的做法应该是由社会监督,由行业学会根据自身行业的内在需求建立职业证书体系。具体建议是成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由著名企业家、教育家、社会人士和政府共同组建,这个委员会是独立的体系,就像美国的国家质量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可聘请CEO进行日常运营,比如把柳传志、王石、张瑞敏这样的热爱公益的著名企业家都吸引进来,包括今天参会的各位专家都加入委员会,做一个二三十年的发展规划。由于这个委员会于当前的政府部门职能冲突不大,只是需要给一个国家的名头增加其权威性,和统筹性。
最后,胡建波教授强调,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这个问题上,他支持俞仲文教授提到了教育版图重构的概念,但作为学校,大家应该避免只盯着产学合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学校发展还是要向国际方面的教育寻找标杆,做好自身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比如大学内部的治理方式问题,大学章程的问题,信息化问题,以及课程规划、教师发展、绩效考核等问题。也就是说任务变了,先要从改变自身做起,而不是就任务论任务,急于求成。(李耀升)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热门图片
Copyright © 职教网 All rights reserved 冀ICP备11020808号-11 全国统一热线电话:400-660-5933
免责声明:本站只提供交流平台,所有信息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害到您的合法权益,请您积极向我们投诉。
本站禁止色情、政治、反动等国家法律不允许的内容,注意自我保护,谨防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