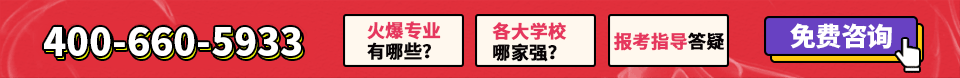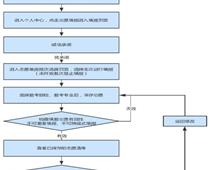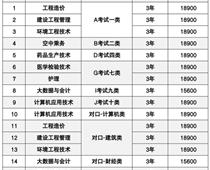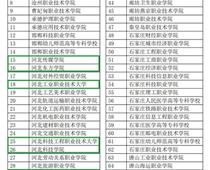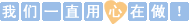《教育哲学》课程作业,用社会学自传的写法写的。字数大概九千多,有点无聊,因为带了一些抽象的分析,慎读。不过总体上都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不同时期的感悟,从幼儿园写到大学,由于最后着急赶ddl,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叙述的不是很好,权当回忆。
上小学之前,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下田地跟大娘干农活(其实是帮倒忙),在院子里拿着棒子追着母鸡打,光着屁股去河套抓鱼,这些就是我五岁前的经历,可以算是最放养的早教了。我四五岁时才学会说话,晋老师曾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并说通常意义上,说话越早的孩子基本上越聪明,我想那我应该就属于最不聪明的一群人了,这也能勉强解释在清华学习比较差的原因。大概是五岁半或者六岁的时候,我家在县里租了个房子,并且在县里最好的小学读一年级(或者是学前一年级,记不太清了),当时我好像是插班生,总共在那里读了可能半年多的书,基本上没留下过什么美好的记忆。有次放学早,我跟一群小孩在学校里踩冰水玩,鞋透了脚冰凉也没什么感觉,一直玩到天黑也没人管,我爸来了之后先是把我臭骂了一顿,然后又赶紧抱起我跑回家把脚放到暖气上和肚子里暖和,倒是有点甜的回忆。印象特别深的是有次学校组织升旗仪式,提前规定好了各个班级站在哪里,当时全校至少能有两三千人,我在嘈杂的操场上找着自己的班级,可能是因为人多或者心情比较紧张,结果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班级在哪,就只能十分尴尬地站在主席台的前面,接受着全校师生的“视奸”(这个词可能有点过了,但我当时确实是这个感受)。与我同样尴尬的还有两个小孩,我不认识他们,我们三个就这么孤零零地站在主席台前,背后台上的大喇叭大声喊着:“是哪个班主任班里的学生,赶紧领回去,不要耽误升旗仪式正常进行。”然后我就看见我的班主任一脸凶相的过来把我领回去了,当时心里十分害怕,感觉回去肯定要挨骂。果不其然,回到班级以后,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台前,还有几个升旗仪式站队不是很好的男生,也都被一同叫到了台前。之后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挨个打手板,口头批评。我觉得打手板其实都还是小事,毕竟疼点也就算了,小孩子记吃不记打,但是当时的言语训斥真的是过于激烈了,激烈到今天的我依然能记得清楚:“连站队都记不住,长大了还能干什么吃的?还上什么学?趁早滚回家呆着得了……真给老师丢脸,全校几千人,就你们三个人找不到位置,还偏偏有你落在咱们班,怎么就这么丢脸呢……”类似的话大概反反复复说了半节课,并夹杂了些侮辱性的词语,台上是一片哭声,台下是鸦雀无声,后来又罚站了我们半节课,这事就当过去了。我那个时候真的讨厌学习,更确切地说是讨厌学校。我感觉周围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家人温暖的怀抱,只有四周完全不认识的同学,还有整天挤兑我的老师。我都不愿意在学校学写字,自己的名字都是在家里被我爸手把手教会的。总之讨厌学习,讨厌学校,想不通为什么家里要把我扔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充满“社会恶意”的地方。两年前坐车途径县里,偶然得知学校原址被拆了,我竟有些莫名的快感。坦诚地讲,从小到大了解、认识、熟知很多老师,即便老师们性格和教育方式各有不同,有些甚至是我不赞同的,但我都挺喜欢并且感恩他们。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让我这么无感过,甚至是有些讨厌。不过也可能是年纪小的原因,对这位老师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也许老师也做过什么好事情,但没办法,小孩子只记仇。这位老师让我的求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对学校的环境有些抵触,客观地讲真算不上什么人民教师。抛开教师基本是每个孩子在走出家庭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类社会中的他者,而孩子对于家庭之外的社会的认知构建通常来源于他最初接触到的其他人。孩子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将决定其对于家庭令其融入社会(对于孩子来说,社会近似等同于学校)这一行为的接受度。事实上,学习的知识的难度、广度、完成度并不会影响到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因为孩子对于环境接受度的判断是通过与周围的人际关系的感知来判定的。对于心智尚在启蒙时期的孩子来说,对于学习这一行为的反馈机制也是通过周围人对自己的情绪来感知的,即便是学习的东西都不会,但如果得到鼓励,也会继续保持强烈的兴趣(我在学写字的过程就是如此)。因为孩子还没有对学的内容有完整的概念构建,或者说这是个形成“对与错”的阶段,因而不会有针对具体行为的反思,而多是观察这个陌生的社会,看看“镜中我”是什么样子的,再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进行调整。谢天谢地,六岁半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市里,我在市里上了大概半年的幼儿园,那段时间爸妈工作在两地,我就跟着我妈住在她单位宿舍,2005年的时候去了市里第二好的小学读书(虽然到我毕业的时候,基本变成了市里的最好的学校之一,但入学的时候还应该只是第二好)。在那里我度过了整体上比较幸福安定的童年岁月,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虽然老师有的时候也很严厉,与同学之间偶尔也闹矛盾,但都是小孩子,这些都不会上心,转眼就都忘了。可能是我小学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小,每天基本都在玩,很少写过作业,偶尔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也不太在乎,最担心的也就是家长会和寒暑假开学前——家长会回来,不论考好考坏,总归是要被严厉地批评一顿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排名高低;寒暑假开学前则是因为要突击补完作业,经常偷工减料地完成(那个时候还比较怂,不敢不写作业,也比较傻,不知道去抄答案,所以开学前经常会变得异常勤奋,有的时候同学之间还互相帮着写)。总体而言,小学期间的我没怎么厌学过,因为基本没怎么学习过,在学校还能跟同学们互相打闹,也有班主任约束着,不让我们那么野。反而回家了只能打游戏、看电视或者自己玩玩具,就还挺没意思的。情况的转变大概是在六年级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即将升学了,虽然当时升初中是按照学区来划分的,与小学时的成绩没什么关系,但一中(全市最好的初中)在入学之后有“回考”,听说还是挺重要的,学习上的压力可能稍稍大了些,老师留的作业也比平时更多了。碰巧,那段时间我比较沉迷几件事:打游戏,写小说,看漫画。学习与这几件事情比起来实在是收益不大,对于一个不知学习的目的和意义为何物的孩子来说,学习只是一项众多平行任务中的被“大人们”所极力认同的,并且逐渐向学生中渗透的评价体系,学生通过这套评价体系可以获得奖励与成就感。而成就感是每个人从小到大,无论是作为孤立的人还是社会中的人,都必然要获得的一种生理需求,与之对应的是意义感,从小到大我们便被告知做一件事情要有意义,要有价值,事实上这便是社会成就感对个人的一种要求和期待。而我当时的评价系统便是根据兴趣来衡量成本,根据成就感来衡量收益,当然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理性的去分析,不过也会朦朦胧胧地感知到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显然,打游戏和写小说都是能够获得高成就感的事物,而看漫画则是高兴趣并且低成本的事物,但学习显然就变成了既没有什么成就感收益(对于小学时排名处于中档的我,并且除了老师家长外,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大家并不是很会根据成绩来判别一个人,实在是难以从学习成绩上获得成就感,而学习的内容也不过是千篇一律,在经历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之后,早就没了对书本上既定知识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并且还要付出低兴趣,高成本的事情(每天做着那些“没有意义”的作业,同时动辄因为“学习态度”不好就要受到批评,而且会耽误很多和同学愉快玩耍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就也挺厌学的,因为学习没有成功扎根到我认同的评价系统中,我自然就不会在意,与其说是讨厌学习,倒不如说是不在意学习。事实上,许多人毕业之后,还会学习读书吗?显然,只要是对工作无益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去做,本质上也是经过这套“成本—收益”分析的。而与大人不同的是,小孩子即便不在意学习,但却会被周围的社会机制所强迫着去学习,由此造成了在其评价系统里其他方面事物的收益损失,自然就会讨厌学习了。这个道理大概等同于正在工地上搬砖挣钱呢,突然有人逼迫你到屋子里坐着学习,学的东西还跟挣钱没什么关系,人都快“饿”死了,哪还有心思“学习”。但是这套评价系统对不同学生的渗透速度和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有的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的多方面熏陶下,接受的快,所以即便是成绩差,但如果认同了这套评价体系,同时又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干扰,那么也不会产生厌学的感受。同时,如果是成绩好但这套体系有抵触的学生,那么也会产生厌学的心理。归根结底,厌学是种态度,成绩是通过影响学生的社会关系(与老师,与家长,与同学),进而作用于学生的评价体系,最后才决定是否有厌学倾向。所幸我很快就毕业了,从小学到初中,是孩子成长比较迅速的阶段,由此我也是摆脱了依靠评价系统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事情,转而进入了全新的价值体系塑造阶段。如果说在2011年之前,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生活中只要快乐就可以,那么从2011年到2017年的中学六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阶段。我身上的文化烙印、生理习惯、为人处世之原则皆是在这一阶段打下的。刚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朦朦胧胧知道现在要保持个好成绩,努力学习,然后争取考上五中(全市最好的高中),之后再争取考上大学,但是这些都距离我过于遥远,家里对我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对我的管控基本还是小学那一套,所以并没有给我增添学业压力。反倒是在初一、初二的时候,我爸有段时间长期出公差,家里我妈也不怎么管我,我在家的时候就疯狂打游戏,在学校的时候就和老师眼中的“狐朋狗友”鬼混,周末的时候就和女朋友出去玩。这段时间我基本变成了个,倒不至于厌学,只是单纯地对学习不感兴趣而已,因为在我的价值体系里,谈恋爱,打游戏,跟老师吵架才是“酷”的事情,学习都是乖宝宝做的,而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个“乖宝宝”。但是从上初中开始,我又接触了长达六年的“全校排名”。这一客观的数字指标,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存在着激励与否定作用。“好学生”、“差学生”、“中等生”各有不同的体验与压力。但总体上,学校作为一种总体性控制机关,它的存在训练了学生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认知。同时也在初步模拟社会上以KPI和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的体系,尽管模仿的很粗糙,但已经在日熏夜染中强化了学生在其价值体系中对于学习的需求。学习,当然是学习新知识,但是工具理性是可以逐渐侵蚀价值理性的,最后演变为学习是为了争取排名。而学生在这套机关里完成“游戏”的水平将决定其收到的“奖励”,显然,奖励的波动和游戏的难度都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情绪。而说是学习情绪,更深层次是客观事实与自身价值体系的契合度。东北的地域文化也决定了“佛系”的人会更多,而竞争的氛围和求学的欲望会被压制。事实上,区别于高考大省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在为高考服务的理念,一切学校里的压力以及学生接受到的来自家庭、教师和其他家庭的压力都是社会压力的真实投射,因而东北社会作为低压力、低欲望、地广人稀竞争少的地方,在学生的价值体系的塑造中,学习固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却并没有那么高。作为贫富差距较小,生活实际质量较高的地区,东北人的价值体系中对于“阶层流动”的感知更弱,落实在学生的身上便是几近没有,由此对于学习的不重视也似乎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在不同的衡量标尺下,不重视的行为就有可能被看成是“厌学”行为。以上三点在我的身上都有着较强的体现,由于它们本身对于学习的态度就是有所冲突的,导致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判断也一直是很矛盾的。同时受到身边朋友和初中老师影响,削弱学习的合法性一直是我的强项,自然就会处于间歇性厌学的状态。所幸高中前两年,不能算厌学,也不能算喜欢,只是很踏踏实实地在学习,更多的时间还是在玩。而且这个时期玩和学习并不冲突,我的高中班主任也是很积极上进的人,可以说帮我稳住了前两个学期的心态,包括对我的很多价值观上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依然在践行着,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感恩的老师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过得比较顺风顺水,虽然偶有坎坷,但成绩基本是每年稳定走高,所以也没有因为成绩不理想而产生过厌学情绪,但会在价值体系与社会摩擦中间断性地产生厌学情绪。事实上,学习作为成人的世界安在孩子身上的一种社会行动模式,学生在接受这套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与日常生活经验,通过人际关系构建出的价值取向等等可能会有所冲突,而一旦发生冲突,学生便可能陷入到对学习的挣扎与喜恶交替的过程中。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会逐步构建起自身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的基石是来自原生家庭、学校环境以及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在未来岁月的成长中,价值体系会根据接受到的信息和经历的人和事不断完善,最终与他者的评价体系共同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情况。因而,在客观的评价体系之外,导致学生厌学的可能因素还有自身的价值体系问题。虽然,到高三的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崩塌了……别人去过清华暑校后,都是对清华充满了向往,然后励志进取,最后在高三学习中披荆斩棘,考入顶尖名校。然而我从暑校回来之后,基本上就进入了长达十个月的“堕落期”,坦诚地讲,如果不是吃高二的老底子,外加上拿到了清华的降分录取,我可能也就无缘这所学校了。如果让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选出段最厌学的岁月,那一定就是高三。刚升入高三的时候,我对学习几乎丧失了动力,一方面是当时的成绩排名,即便在自己很浪的情况下,也能排到前三的水平,虽然后面有些下降,但也只要稍稍认真学一段时间就能追回来,没有了排名的激励,而我又不是喜欢追逐第一的人,自然也有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对于生活失去了新鲜感,当到了高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好好学习了,加上分班调整的时候,最能玩的几个哥们都因为成绩差了点调到其他班了,整个班级仿佛一瞬间变得好学了起来,只有我还沉浸在轻松自由的惯性中,每天放弃学习。最后就是我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意义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无论是成绩也好,排名也好,大学也好,我们所有的成就,所拼命追逐的东西,也不过如此,那我凭什么要为这些充满虚无感的事情奋斗呢?换言之,高三的十个月,是我前十七年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崩塌的十个月,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在破碎地重建着。我失去目标感了,无论是能否考上清华,抑或是其他学校,这些与我何干呢?我自信将来能够吃饱饭,又没有挣大钱的想法,每天只要过上读书、睡觉、晒太阳、教教书的生活,就够了,那么我像大家一样拼到身体不行,到底是图什么?我失去意义感了,学习变成了枯燥的、重复性的东西,每天只是像工具人一样去准备高考,可能是骨子里的性格让我对这种状态感到抵触。除了交到的朋友,留过的回忆都是真的,其他的东西都不再能带给我意义感,生与死,富与穷,高低贵贱,都是他者的看法,我需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大概就是吃饱了撑的时候的想法。我失去价值感了,我不知道怎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以及自己是否真的有价值。我会时常思考人类社会乃至宇宙存在的客观价值是什么,但是没有头绪。而我自己的主观价值,我则清晰地意识到是被现实社会建构的,我极力地想在这种价值之外找到一种符合自己生理和精神需求的价值感,也许读小说和写作算是,但遗憾的是,高三期间并没有找到。每天在学校重复性的生活很无聊,只有体育课最让我兴奋,那时候还很不能理解体育课在屋子里学习的同学们,我都是放飞自我地出去踢球或者打球,总之只要能出去,我就绝对不在教室里呆着。有时晚自习如果是一些管理很松的科任老师来讲课,我就会悄悄溜出去到操场上玩。即便是平时老师在讲正课的时候,我通常是在下面看语文卷子上的小说,高三一年大概看完了十几本练习册上的小说,或者是解一些很难的数学题或者物理题,再就是把一些老师留的作业在课上写完(这也是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做法)。基本上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情况,完全脱离了学习场域的要求而独立行进的轨迹。高三中后期的时候,我热衷于在午休的时候读长篇小说,东北的冬天和早春都是寒冷的,教室里即便有供暖也是冻的人瑟瑟发抖,我在教室里养起了小花;每天在大家第一节课下课都睡觉的时候,下楼把水桶扛上来,做做值日;午休的时候跟两个小傻子在食堂交流最近的八卦,互相调侃;晚自习的时候跟同学激情地打打水仗,或者给女朋友讲讲题;晚上回到家以后看看小说和电视,差不多就睡了。《平凡的世界》可能也是影响我比较深的一部小说,最开始是在高二读的,后来升高三之后反反复复读了五六遍,针对这本书的感悟实在是太多了,单说对我生活态度的影响:从此我对生活的追求不再是线性的,无论哪一种生活其实本质上都是“平凡”的,而无论哪一种生活,阶层上升也好,阶层滑落也好,生老病死也好,喜怒哀乐也好,都是“真实而自然”的生活。想通了这点后,我便更加坦然地消除了由于“不学习”而带来的“内疚感”。坦言之,从他者的角度看,尤其是没有过我这番体验的人眼中,这些都可能是自傲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自傲会有维持住自傲所需要资本的动力需求,而我当时对成绩是完全不在意了,无论考的高还是考的低,最多也就在出分的时候带来些紧张感,然后便再不能对我有任何影响。考试对我完全变成了一种工作,而我在学校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让父母和老师放心,学习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事物。每到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和女朋友出去玩,而是独自地,漫无目的地,自由而失联地走在家乡小城的街道上。高三一年,基本上把我们家那个不大的小城逛了个遍。高考结束,我比所有人都紧张,也比所有人都轻松。无论是出分还是录取,都没有在我心中惊起任何波澜,会有些遗憾,没能为我的高中班主任争脸,我很喜欢他;但也都过去了,出分那天下午五点,我的老师,我爸,还有我,三个人在小区楼下吃了顿羊肉火锅,我爸很激动,老师对我叮嘱了好多,只有我心里平静的像死了一样。我以为生活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告别冰冷燃烧的过往,在大学里能重塑价值体系。之前积累的这些厌学原因,总的来说,问题大多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并不会因为换个环境而有多大的改善。刚进清华的时候,的确一切都是新的,然而一切又都是陌生的。作为全国最顶尖的学府,在进来之后还没容我喘过一口气,就会用学业负担重重地鞭打我。但接受过高三这么长时间虚无挣扎的我也就是略微感到不适应,随后很快便调整过来,继续放任自己。我在学校里默默行走着,观察着,经历并体会着不同的人和事,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我逐渐的开始反思整个学校和社会。如果说大学之前的我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的经历来感悟厌学的原因,那么大学之后我开始使用结构的视角来看待不同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随后再对应到自己身上,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等我到大一下学期接触一些社科理论和哲学思想后,我开始尝试反思并“拯救”自己,试图走出这种状态。然而诸多理论和思想并没有让我对生活变得更积极,反而是让我更清晰地对自身的处境、存在意义以及社会价值进行了解构。(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我还试图拯救处于厌学状态的我,不像现在,已经坦然接受了这种状态并且十分乐观积极地认为这才是自然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解到诸如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这样的词,开始认真剖析自己对生活没有感觉并且厌倦学习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为自己的状态感到疑惑和羞耻,而是为世界上还有能够共鸣和学习的知音而欣慰。我决定放弃对旧有价值体系的追寻和挽回,在自由而无用的生活中开始拼凑起全新的、属于我对世界思考的、又带有之前的许多惯习的,价值体系。对原来学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就转到了社会学系读书,纯当是体验不同风景。虽然有很多人对我工转文的事情不是很能理解,认为收入会变低,前途会变暗之类。然而我知道所谓的收入我不在意,过上我想要的生活肯定是足够;所谓的前途并不是我想要的,别人觉得变暗那就变暗吧。但内心深处我是知道,因为我的本科学校是清华,所以我可以有恃无恐,不必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不用累死累活也能过上可以接受的日子,自然就不会担心学习不好带来的种种恶果。可以这么说,清华本身的名头,恰恰是我厌学的底气之源。然而转到社会学后,学习态度并没有因为学的内容变成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更积极了。我依然消极着,散漫着,直到今天。这可能与清华本身的课程设置有很大关系。即便是转到社会学系之后,也很少有我十分感兴趣的课程,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已经逐渐实现高三时的理念,也就是靠自己读书和实践。如果从社会和学校的角度评价,我肯定还是处在厌学和逃避学业的状态中。但如果从我自己主观对学习的界定来看,我已经逐渐走出了厌学的状态,并且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领域和感兴趣的事物,只是与大学本身之要求不太相符罢了。当然,社会学在推动我解构自我,解构社会,分析重建价值体系过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系有句话说得好,学完社会学,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出家了。倒也不妨为很多时候我的真实心态。最后是我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当一个人有理想并且能够最大限度摆脱结构的压制时,他就会变得无所畏惧。而我的厌学,固然仍然有很多虚无感的缠绕以及关于终极问题的困惑,但是学习本身于我本身,于我的理想,都没有过多的帮助,我只要能够拿到学历文凭,获得理想的准入证,那么剩下的生活将是我自己打拼的,像课程学习这些无关的沉没成本,自然要被抛弃。这里似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成本分析那里。不过总而言之,现阶段我的学习只为三件事服务:兴趣、价值、理想。如果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与我未来的理想没有什么关系,那我索性不学好了。但我依然重视着在大学的种种生命体验,因为这些经历是独一无二的,超脱于兴趣、价值与理想之上,无论我将来行走到哪里,都不会放弃每一分每一秒、不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经历。我现在还不能给厌学史画个句号,也许等某一天我真的尘埃入土了,再回首这一生时,才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自己做出的每个社会行动,以及其背后的意义与社会意义。我们终究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寻意义的,我也在努力地实践着,热爱着自己的生活,并为自己的每个行动赋予意义。也许这般思考和意义的赋予在别人的眼中看来有些无趣甚至可笑,不过。也许当我将来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当我再次接触全新的人、全新的事、全新的城市的时候,我会在熟悉、解构、反思、赋魅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生活态度与价值体系。学习是前二十几年的主线,后面要经历的精彩事情,还多着呢!回首过去的二十年,我的生活可能就是运气过好,侥幸太多。比如小升初的时候,家里在三年前买了学区房,刚好卡在了政策线上(从那年开始不再能通过择校费而跨学区入读);比如中考的时候,成绩处于全校巅峰,还在思考要不要去长春读书,结果一下子考砸了,却又砸的刚好能进入五中A班读书;高考的时候,虽然堕落了一整年,但也勉强靠着降分苟进了清华;大学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想要放飞自我理工转文科,也顺其自然成功了。顺境可能会让人放松,让人失去短期内想要实现的目标。而我这种顺境又是刚好在每个阶段都能够得到世俗最满意的位置,而我自己又刚刚好喜欢的位置。于是来自内外的压力便都消失了,给了我遁入存在主义的可乘之机。然而具体到每个人生阶段去看,又能看到原因是如此的不同。从社会关系对个体在学校环境的影响,到他者评价体系对个体的激励与否定,再到价值体系建构后,个体追寻本心认同的“价值”时偶尔与社会的冲突,随后是意义感剥夺时,学习作为社会行动之一受到的影响,最后是尝试解构学习这一社会行动和赋予生活意义时对世俗认可的学习行为的反思与判断。由此种种,从外到内,构成了我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厌学史。当再度回忆求学生涯时,我也会怀念那个在2003年夏天,光着屁股,拿着板锹,在田间地头自由漫步,浑身全是泥巴的小孩子——或许那才是唯一快乐学习的时光。